九游娱乐-澳洲人文队挑战考验,艰苦争胜
文/忆殇
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,活跃在当下的顶级学者很多出自于北大,如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、陈平原等人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王瑶先生的学生。王瑶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,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,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学生。温儒敏写了一篇《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》,来怀念他们承教于王瑶先生的经历,老师的敦敦教诲、学生的求知若渴都令人无比神往。
1978年是恢复研究生招考的第一年,北京大学共招收了19名研究生,其中现代文学专业7人,包括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、凌宇、赵园、陈山以及张枚珊(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)。导师王瑶、严家炎自不必说,这几个学生之后也都成为现代文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。其中,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所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,三十多年来历久不衰,成为每一个中文系学生绕不开的经典之作。凌宇是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,赵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陈山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、博导,每个人的成就都对得起老师的教诲。这样的老师,这样的学生,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是很难见到的。
每个人的青春岁月,尤其是大学时代,所遇到的人、经历的事,所接受的价值观熏陶,很容易影响一生的走向。“人生的路可能很长,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在年轻的时候。也许就那几步,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。”(温儒敏《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》,下文除特别标注外,皆引自本文)建国后,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,高校停招,温儒敏等人被迫多年从事与个人志向相悖的工作,他们是不幸的;然而,随着1978年研招恢复,他们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,并且牢牢地把握住了,他们也是幸运的。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政治运动停止,思想空前解放,学界思潮汹涌,校园空前活跃,物欲膨胀对做学问的滋扰还很小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得的一段潜心学问的好时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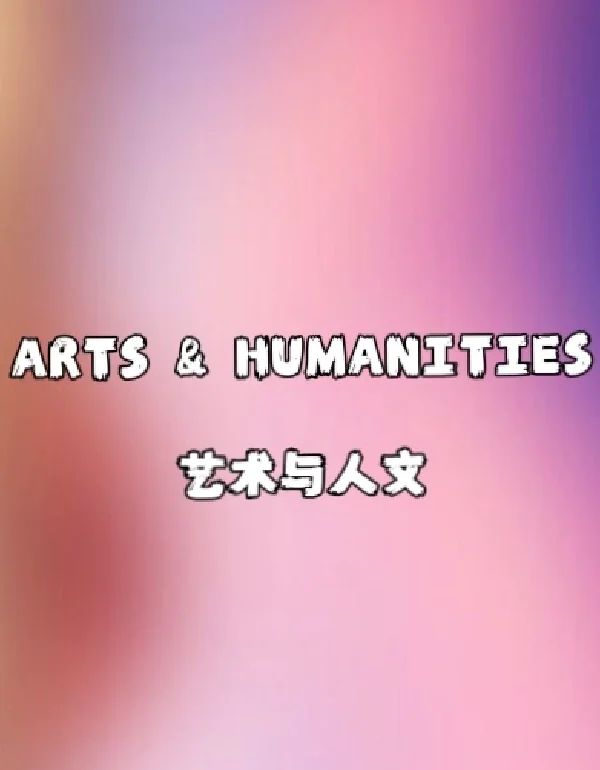
温儒敏是这几名研究生中最“年轻”的,时年32岁,年纪最大的钱理群、吴福辉已经39岁了。入学之前,温儒敏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了7年的秘书,钱理群更是在贵州安顺做了18年的普通老师。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里,他们远离自己醉心的学术,对自己的前途茫然无知。这不仅是他们的损失,也是学术界的损失。幸运的是,他们从8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,成为了恢复研招之后的首批研究生。北大是很多人的梦想,他们不仅考进去了,还遇到了王瑶、严家炎这样的导师,前半生的苦痛也就微不足道了。
这几个老“青年”就像刚读大学的新学生一样,既新奇又兴奋:“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,十多平米,4人一间,挤得很,但心里是那样敞亮。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(老师也是这种校徽),走到哪里,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。”实际上,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人,有各自的家庭,拖家带口,两地分居,虽有工资却少得可怜,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机会得来不易,他们自然倍加珍惜。“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、咸菜和玉米粥,就到图书馆看书,下午、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,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,是常有的。最难的是过外语关。我们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,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。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。”赵园也曾回忆这三年读研生涯:“这帮人起点不同,经历各异,但好不容易‘重返校园’,都很玩儿命,相互之间也不免暗中较劲。都有了一把年纪,遇到一起,很投缘,这尤其不容易。”虽然生活艰苦,读书枯燥,但强烈的求知欲却让他们将这些抛之脑后。年纪即长,他们自然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,这个过程就像跟时间赛跑,已失去的追不回,眼前的自要紧紧抓住。学术是十分枯燥的,文学这个领域更是如此,大量的作品要读,相关的评论要看,基本的史料要掌握,没有一番苦功夫是不行的。“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,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,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。”三年时间,一千多种书,还要上课,从头学外语,写论文做研究,温儒敏等人给后人提供了“大师养成记”的范本。
学生肯努力,老师也足够优秀。王瑶先生师从朱自清,在中古文学史、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三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,他所著的《中古文学史论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影响深远。严家炎先生也是现代文学领域的顶级学者,他所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(与唐弢合著)、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同样影响深远。温儒敏详细描述了跟随两位导师求学的经历,以及当时北大颇富特色的教学方式,令人不禁心生神往。“先生(王瑶,笔者注)是有些魏晋风度的,把学问做活了,可以知人论世,连类许多社会现象,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。先生的名言是‘不说白不说,说了也白说,白说也要说’,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。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,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”王瑶先生对学生要求颇为严厉,同时又因材施教,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指导研究的论题。温儒敏等人常能在课堂之外聆听王瑶先生的教诲:“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,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,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,引经据典,天马行空,越说越投入,也越兴奋。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,连喘带咳,说话就是停不下来。先生不迂阔,有历经磨难的练达,谈学论道潇洒通脱,诙谐幽默,透露人生的智慧,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。”这让人想起徐志摩在《吸烟与文化》里说的一个段子: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。导师的秘密,按利卡克教授说,是‘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’。”文学研究不是一门“一是一、二是二”的学问,正所谓“诗无达诂”,对同样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演绎与理解,它是一门活的学问。只知教授学生文学史实是不够的,更重要的是开拓思路,与严肃的课堂讲授相比,课外的随性交流更能激发学生的灵感。“那时还没有学分制,不像现在,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。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,但更有自由度,适合个性化学习。”温儒敏等人正是在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下,完成了最初的学术积累。
“有一种说法,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‘从游’,如同大鱼带小鱼,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,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,长成本事。当年就有这种味道。”当时带领温儒敏等“小鱼”的“大鱼”不止前面两位导师,而是集体成果:“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,孙玉石、唐沅、黄修己、孙庆升、袁良骏,以及谢冕、张钟、李思孝,等等老师,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。校外的陈涌、樊骏、叶子铭、黄曼君、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。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。……孙玉石、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,在老二教阶梯教室,200多人的大课,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,我们一节不落都跟着听。……语言学家朱德熙、岑麒祥、文字学家裘锡圭等,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,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。”一个导师的修养、气质、治学思路,很容易传达给他的学生,即使这位导师再优秀,也难以身兼百家之长,他对学生的影响越深,越容易限制学生的发挥。我们常说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人类文明之所以不停地发展、进步,正是因为后代人不是对前代人的简单继承,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。北大历来有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传统,正是有如此多的优秀导师教给了学生们不同的知识和理念,才让温儒敏等北大学子站在了学术界的顶峰。
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、自由的年代,各种新思想、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,温儒敏等人受益于这个年代,他们得以充分思考、吸收,进而贯穿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。“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、选择的机会,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,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。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。”如今的大学校园很难再出现这样的盛况,难有王瑶先生这样的导师,也难有温儒敏等人这样的学生。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抹不去的悲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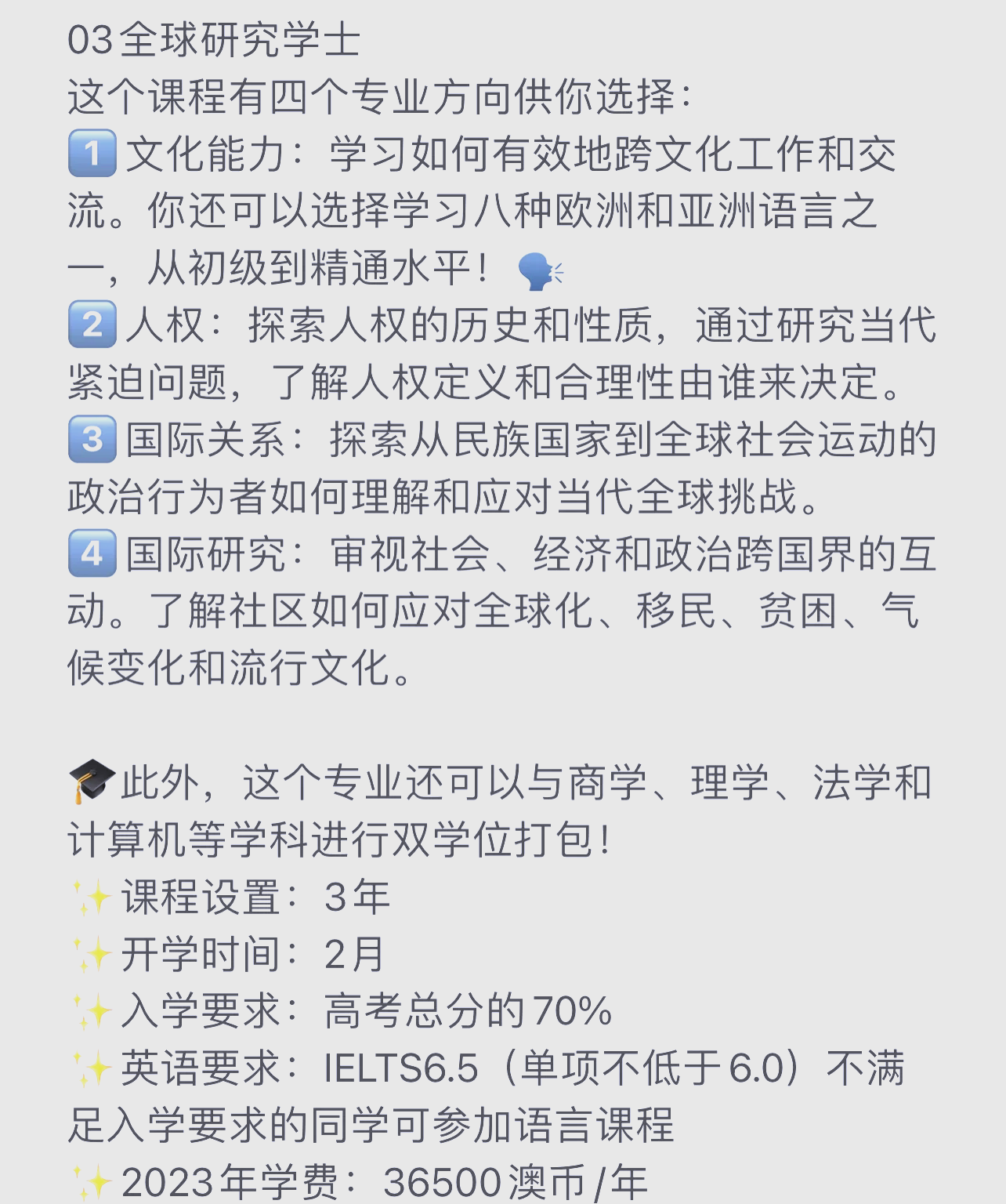
止点:剖析社会万象,品评天下文章,书写人间悲喜。愿更多人感受到文字的温度和思想的力量。欢迎关注公众号“止点”,转发朋友圈。



评论留言
暂时没有留言!